
我首次踏足維也納,乃是一九六三年八月下旬,從貝爾格勒搭火車去。
出火車站不遠,我找到一間昏暗骯髒的「旅館」。
我這輩子沒住過那麼糟糕的旅館,可怕程度連塞維爾的工人平價旅社都比不上,房間裡臭蟲、蟑螂橫行。但我只住得起那間旅館。
其他垂頭喪氣的房客,帶著以粗繩捆紮的卡紙板手提箱,來來去去,但都住不久。
我則住了很久,因為我在隔壁街認識了一個好心的當地人,可以去他那裡喝湯吃麵包打發三餐,有時,大概每隔幾天,我還會犒賞自己一杯澀味白酒。
1683年,整整280個夏天前,前來圍攻維也納的奧圖曼大軍,就在那個地點紮營。
那是歷史上土耳其人第二次圍攻維也納。
1529年秋,第一次圍攻時,他們就來過那裡。
當然,1963年時,已沒有蛛絲馬跡或回憶可追溯那兩場惡戰,而我也幾乎未聽人談起它們。
能見到的,就只是更晚近一場攻擊留下的痕跡。
1945年,蘇聯第三烏克蘭戰線部隊與納粹武裝黨衛軍打了十二天的巷戰,最後於四月十三日拿下維也納。
十八年後,我仍可在一長條公寓大樓的正立面高處,見到當時留下的累累彈痕。
在那幾個月前,我在馬德里人文學院後面停車場牆上,見到一樣的痕跡;
在我們上課的那些房子裡,共和派曾拼死奮戰,逐樓撤退,最終擊退佛朗哥將軍非洲兵團的進擊。
那是1936年初冬的事。
在維也納見到那些彈痕,立即叫我一陣戰慄:我知道它們的來歷。
雖然距當時那麼遙遠,此刻沉浸在生機勃勃的維也納飲食、藝術、音樂、文化中,當下的感覺也與一般人無異,
但我還有種不安,對戰爭、暴力、生死搏鬥的不安。
我祖母曾是奧匈帝國子民,對一九○八年之前的事,懷有浪漫回憶。
十八歲時的我,滿懷祖母所灌輸給我的那些回憶,覺得維也納既迷人且叫人有點失望。
但那些彈痕累累的牆——在有些地方那就像張醜陋的大麻臉——卻在我腦海徘徊不去。
第二次來時,我至少對1683年土耳其人圍攻市中心的事有所了解。
約翰.史托耶的《維也納攻防戰》是我的旅遊指南,當時才出版不久(1964)。
我每天沿著同一條路線,在市中心穿街過巷,試圖將1683年所發生的事與矗立在該區的建築串連在一塊。
城裡大部分地方,街道布局和1683年時大同小異,
但這時(還未列為「世界遺產」之時),已沒有標記或牌匾可訴說數百年前所發生的事。
我很快設立了自己的地標:
一家販賣美味新鮮香腸、外加一碟泡菜、一份油亮亮馬鈴薯沙拉的肉品店;一間供應平價好葡萄酒(九、十月時最佳)的破舊酒吧。
後來,我搭電車到城外格林欽的葡萄酒村,或搭火車到克洛斯特新堡大隱修院附近的酒館,找到遠遠更好喝的葡萄酒。
但接下來幾十年,我那些常去的老地方漸漸消失,雖然不像其他歐洲城市裡消失得那麼快。
1980年代地鐵的建造,標誌著1914年前舊世界的終結;
那是自一個世紀前拆除舊城牆、建造環城大道之後,維也納最浩大的營建工程。
或許表面上看來是如此。
事實上,那反倒促成舊世界的重見天日。
原據認已拆掉的舊城牆和稜堡,其實仍存在於這座十九、二十世紀新城表面底下,至少仍存在痕跡和基礎。
我告訴一友人,在國家劇院附近見到有人在挖掘。工人挖地基,以便建造新辦公大樓,結果挖出像是舊拱頂的東西。
牆與瓦礫的顏色古怪,很淡,我不確定是磚造還是石造。
他說他知道我看到的是什麼:維也納城牆。
1850年代起,環城大道工人將城牆一塊一塊拆下,拆到地面下一點點時就停手,以便為這道路工程留下堅實的路基。
因此,維也納城牆,或至少該城牆的殘餘,仍在原處,
一如俄羅斯人進攻該城所留下的痕跡,在1963年時仍在原處一樣,如果你知道去哪裡找的話。
知道歷史事件在哪裡發生,很重要。
四處走覽是不錯的點子,但地理景觀往往已不復原貌。
不過,在這段歷史於筆下漸漸成形且筋肉日趨壯大時,我另外去了一些戰場和其他可憑弔歷史的遺址。事實上,那些地方多是歷史湮沒不明之地。
在那裡,沒有人知道遭遺忘已久的戰役曾在哪裡開打,甚至沒有人講得出那地名。
有時我運氣較好。在現今奧地利、匈牙利交界上,大約在莫格斯多夫村附近,聖哥達之役的遺址上頭,有座小丘俯瞰戰場。
當地一位熱心人士和村民,在小丘上蓋了座小型紀念館。
那場戰役是莫格斯多夫村最重大的歷史事件。
但那紀念館所記錄的,只是漫長複雜歷史裡的一刻,從歷史割離開來,而看不出來龍去脈。
****
因此,這不是段容易理解的歷史。
由於某種和恐懼(我主要的研究課題)一樣短暫且難以捉摸的東西作祟,我不清楚什麼東西會是重要或有用。
後來,因為研究奧圖曼匈牙利史卓然有成的史學家帕爾.佛多爾指點,我才了解為何會有這樣的事。
有天,在布達佩斯,走出科學院時,他告訴我,對於在奧圖曼匈牙利境內發生的許多可怕之事,我們知之甚詳。
我們可能知道某種暴行在哪裡發生;甚至可能知道誰受害或知道他們的遭遇。
但這些可怕之事,都未能創造出適用於所有類似情況的一般概念,一貫說法。
每件事都是獨一無二,除非我們能切實提出那事的普遍之處。
歷史一團亂,通常叫我們吃驚。
我在無意間走進一塊遼闊而只有局部耕耘的領域。
關於十五、十六世紀,已有大量優秀作品問世,關於十七世紀,少得多,關於十八世紀,則幾乎沒有。
因此,我把焦點放在這段較晚的時期,以1683年維也納城攻防戰為核心,直到哈布斯堡和奧圖曼土耳其這兩大帝國衝突的最後時期為止。
為使故事不致龐雜失控,我不得不略而不提這場對抗奧圖曼帝國的戰爭中其他的參與者,
不得不捨棄有關維也納之角色與在伯羅奔尼撒半島、島嶼、地中海所發生之戰役的資料。
有關克里米亞半島和俄羅斯往東擴張、最終將勢力伸入中亞諸汗國的資料,也有很大部分不得不割棄。
我不得不百般不捨地擱置我對中國的冗長補論。
就奧圖曼、哈布斯堡後期的軍事對抗來說,最晚近的原始資料,仍是那些寫於十九世紀的資料。
這場聖戰曾占據歷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許久,但老實說,到了聖戰晚期,該聖戰已跌出歷史重心的舞台。
第一次到維也納之後的幾年裡,研究之路未把我引向十七世紀的軍事史,而是十九、二十世紀的軍事史。
檔案室裡的爬梳,重點放在奧地利於國際武器買賣裡的角色,我在小鎮施泰爾,埋首於當時的航海日誌和存貨清單,度過快樂的幾個星期。
我從那裡去了維也納戰爭檔案館的密室數次。但一直以來,在許多史料裡,都潛藏著某種未明言的恐懼:
恐懼競爭者或對手會取代奧匈君主國;恐懼未做好準備,恐懼科技落後,技不如人。
最後,當我轉而探討其他哈布斯堡的主題時,仍察覺到這股幾乎未曾消失的隱隱焦慮。那焦慮從何而來?
****
大部分歷史需要在探討開始前預為解說。
首先,我得益於一些學者的研究,也就是說,我的想法承襲自某些學者。
我想寫這主題想了很久,但若沒有羅德斯.默菲的《奧圖曼戰爭,一五○○至一七○○》在一九九九年出版,卡洛琳.芬克爾《奧斯曼的夢想:奧圖曼帝國一三○○至一九二三年史話》在二○○五年出版,這本書不可能寫成。
當代出版品對於「土耳其人」那種根深蒂固的負面看法,我從來不信。
我可以說明這些負面觀點如何透過書籍、小冊子、繪畫、版畫、甚至茶杯和瓷磚,在西方世界一個接一個滋生,但我提不出另一種看法。
默菲和芬克爾摒除了某些刻板觀點,但更重要的,他們也縮小了雙方在戰場作為上實際的差距。
西方作家認為「土耳其人」的行徑超乎人類正常範疇——殘酷、好色、受盲目信仰不斷的驅策,
因此,在他們筆下,土耳其人無異於人格變態的民族,
奧圖曼帝國幾乎不可能有別的行徑,例如人道行徑。
但這一形象根本與實情不符,從法醫學角度得到的證據,均一再顯示那些刻板看法不實,令人不安。
另一位對我思想有所啟蒙者,乃是奧地利社會人類學家安德烈.金格里奇。
大部分資料,還有我對歷史事件的較深入研究,都不適用於任何思想架構。
金格里奇將對西歐以東地區所發展出來的觀念——從該地區的民族和文化發展出來的觀念,稱作「邊境東方主義」(frontier Orientalism)。
我嘗試以這概念去解讀我的資料——那些資料前後涵蓋的時期,比金格里奇原本所描述的時間更長得多。
結果管用。
這概念給了我一個基本模板,讓我可將一個個證據像拼圖一樣拼出完整面貌。
我想未來史學家會發現「邊境東方主義」是個無限好用的觀念。
我並非根據原始手稿寫成(只有一兩處例子用到原始手稿),而是根據十六到十八世紀出版的資料寫成,當時人對那些事件的了解,想必大部分得自那些資料。
那些是我已研究了二十幾年、至今仍在研究的資料。如今,我仍在發掘遭湮沒的歷史,且也正在改變對已研究過之資料的看法。
偶爾,我們無法得知人如何形成其看法,但我們可以了解資料如何呈現在他們眼前。
自十五世紀迄今,情況改變不大。
一如你讀到這時,有人決定將這個作品出版,希望從中獲利。
有些書、小冊子的印刷出版,出於別的動機,但我所用過的資料,大部分清楚屬於營利性質。
它們是待賣的產品,而印刷業者(當時的出版商)努力使它們盡可能為潛在顧客所買走。
促銷的關鍵手法之一,乃是替它們配上雕版畫、木刻版畫插圖。
在識字率較低的年代,這特別管用。
欲了解某書是否大賣,方法之一是查明印了幾版,在市場上賣了多久。
同樣的,如果某書出版了別種語言版本,那書想必又得到了新一批不同族群的讀者。
我們慢慢查探這些網絡。
有些書籍催生出為整個歐陸人民所信持的看法。
英國人保羅.萊科特的著作,出版了好多版且譯成法文(兩次)、荷蘭文、德文、義大利文、波蘭文、俄文;
維也納被圍期間一直住在城裡的律師約翰.彼得.馮.費爾克倫,寫了一本小書,一六八四年在布魯賽爾出了法語、拉丁語兩種版本;在林茨出了德語版;在維也納、威尼斯、那不勒斯出了義大利語版;在克拉科夫出了波蘭語版;在倫敦出了英語版。
還有一些書只是剽竊已出版書籍的內容,掛上不同書名出版。
手寫稿是最普見的傳播方式,但傳播範圍相當有限,而印刷書、木版畫或雕版畫、或小冊子,則是為了大規模銷售而問世的東西,是可買賣的商品。
從這角度來看,後人所收藏之印刷書珍本上的記述,往往比大檔案館所收藏之手寫稿的內容,更能揭露大眾的態度和看法。
如何才能理解真正發生的事?
可以用華麗的「文明衝突(與失敗)」思想模式檢視那事,結果頭一次檢驗證據,那模式就不管用。
可以審視「穆斯林衰落」這觀點:從中世初期幾場大勝之後,穆斯林就步上漫長的江河日下路程。
但我也不覺得這觀點站得住腳。
我用了不同的措詞。
我談(奧圖曼)「土耳其人」,而非「穆斯林」。
奧圖曼帝國是非常虔誠的穆斯林,但除了瀰漫奧圖曼帝國的伊斯蘭文化,他們還有明確的突厥語族文化傳統。
近來,史學家避用「土耳其人」一詞,原因是奧圖曼帝國認為「土耳其人」是鄉巴佬,覺得被叫作「土耳其人」是一大侮辱。
的確如此:但在這同時,他們也極自豪於自己的土耳其先祖和出身。
再怎麼說,突厥語族認同,為凱末爾的新國家——土耳其共和國,提供了意識形態。
哈布斯堡王朝在偶然間成為奧圖曼帝國在西方長久的死對頭。
波蘭人、匈牙利人也有各自一段與奧圖曼帝國衝突的歷史,那是與哈布斯堡、奧圖曼帝國衝突史有所不同且同樣重要的歷史。
但奧圖曼、哈布斯堡的對抗,是兩個「帝國」的對抗,雙方都想取得某種支配和管轄權。
兩者共通之處較多。這兩個古老帝國,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滅亡,但在滅亡的許久以前,就老朽不堪(在其競爭者眼中)。老朽不堪的認知、古老過時的儀式、十九世紀末期對他們老態龍鍾、看笑話式的包容,這些不只在一九○○年時不符事實,且還歪曲了他們的歷史。
本書以兩者歷史開始合流之時為開頭,以兩者不再相互殺伐之時作結。
戰爭能揭隱發微,診出弊病,就像具折射力的稜鏡,能將錯綜交織的問題分解為各自的基本組成。
它幫助史學家提出(並回答)以下問題:奧圖曼政權為何落敗?
怪的是,失敗的哈布斯堡政權,卻沒有受到以同樣問題如此追根究底的質問。
我的作品不是部軍事史,重點其實在探索社會如何因應這主要挑戰。
若欲了解那段歷史,套句約翰.基根那個震聾發聵的觀點,我們得了解奧圖曼帝國的「戰役之面」。
~節錄自《1683維也納攻防戰:哈布斯堡王朝與土耳其人的對決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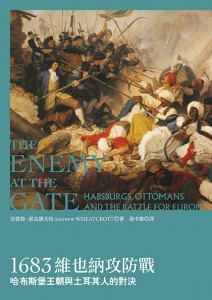
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